“我們雖然是游戲的參與者,但我們必須制定游戲規則。在我們的游戲規則之下,供應鏈各個環節的人們開始把上下游的各方視為團隊而非獨立個體,他們開始互相達成理解。”
2007年10月接手TCL多媒體CEO一職的新加坡人梁耀榮,給TCL帶來的不僅是一份扭虧的財務報告,更多的是國際化企業中的規范流程和行為模式。事實上,這位擁有多年跨國企業高管經驗的職業經理人,并不缺乏李東生所倡導的“企業家精神”,56歲的他看起來依然干勁實足。
《中歐商業評論》:您為何會從飛利浦順利退休后選擇加盟TCL多媒體?
梁耀榮:飛利浦是TCL的戰略合作伙伴,兩家公司關系一直很好。每兩年,李東生先生總會和飛利浦的很多董事會成員坐到一起來審視過去的業務。這么多年下來,我們就像一個小家庭那么融洽。我退休后,李東生正式向我發出加盟的邀請,開始我還有些猶豫。最終作出這個決定,主要是因為過去良好的合作關系,以及被一種自我實現感所驅動,我想要做好一家正在國際化道路上前進的中國企業。
CBR:能告訴我們您加盟時TCL多媒體的狀況嗎?
梁耀榮:當時TCL正處于恢復期。我加入時它已經度過了最艱難的時刻,財務狀況正在逐漸好轉,但還有很多事情要做。那時TCL的狀況可以被概括為三點:第一,公司已經意識到國際化的過程充滿挑戰和風險,用中國話來說就是“交學費”,當時集團已經能從正確的角度來認識面臨的問題;第二,公司當時已經開始通過國際化在全球建立品牌知名度以及客戶關系,這些都是寶貴的財富;第三,積累了一批具有國際視野并且會說外語的人才,并逐漸建立了國際化的信心。同時產品形象也跟隨市場改變,開始從傳統的顯像管電視生產商轉變成為現代化的平板電視生產商。
CBR:能否介紹一下您成為CEO以后都做了些什么?其中,最核心的是哪一塊?
梁耀榮:回顧我來TCL多媒體一年的時間,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理解和溝通、建立流程、業務管理和控制,或者說將各項流程連接起來。
開始的兩個月我試圖理解這個公司,我用了很多時間和公司的人員交流,制定計劃。盡管我過去和TCL打過多年交道,并且從1978年起就在中國工作,也在中國做過并購,但那都是從外國人的視角來看中國。這一次要從內部人的眼光來看一家中國公司并領導它,對我來說依然是巨大的挑戰。
第二階段我花大力氣建立了很多流程,譬如成本透明化、供應鏈管理、參照市場標桿制定薪酬和激勵體系,以及建立與媒體和投資者溝通的規范化體系。
第三階段是加強業務管理或業務控制,我們正在試圖把各項流程連接起來,使得業務的響應時間盡可能縮短。比如產品成本和毛利潤,這些都是在不斷變動的,如何將它們端到端地連接起來呢?這很難,也是我們現在正在做的核心工作之一。
借助“計劃” 重新制定游戲規則
CBR:出于平板電視對供應鏈的速度要求,您對TCL多媒體的供應鏈管理做出了哪些具體的改變?
梁耀榮:我們開始重新加強關于“計劃”的概念。比如預計到了某種元件有需求,再下訂單,這要求必須事先計量。因此,我們給供應鏈的各個環節都設立了訂單計劃指標,也就是說,經銷商向我們有計劃地下訂單,構成“訂單計劃”,我們進行分析后,根據能力和情況,和經銷商達成一個持續性供貨協議,然后再根據協議進行生產,計劃一旦制定不可隨意更改。這是“供應計劃”。此外,經銷商還需要完成一定的銷量,這是“銷售計劃”,我們將這些環節連接起來,并在每個環節設立考核指標。通過這種“計劃”的方式,重新制定游戲規則。
在此之前,銷售商的要求很多,我們的工廠為了滿足他們所有的要求,常常疲于應付。這導致兩種情況的發生:第一,我們試圖滿足他們,但他們永遠不會真正滿足,也永遠不會感謝我們;第二,因為我們很努力地去適應那些不斷變動的要求,從而導致自己的成本升高。
我常說,我們雖然是游戲的參與者,但我們必須制定游戲規則。現在,如果對方對我們提出很多新的要求,我們就會給他算賬:這會耗費我們哪些方面更多的成本,然后反問他,“你會給予財務補償嗎?”當然,他會說“不行”。就這樣,在我們的游戲規則之下,供應鏈各個環節的人們開始把上下游的各方視為團隊而非獨立個體,他們開始互相達成理解。
現在,我們已經能達到這樣的程度:中國的銷售經理和采購經理坐到一起,開始審視供應鏈上的關鍵環節,比如液晶屏,他們共同決定是否需要采購這款屏幕,因為如果這款屏幕不能及時做成電視機賣出去,它的貶值將非常快。當人們坐在一起時,他們必須對每項采購計劃作出判斷和承諾后方可執行。
而這在以前,往往是最高管理層決定的事,執行層面的人根本不會去考慮。現在這種制度做到了雙贏。為此,我們用了5~6個月的時間,讓生產,銷售和采購三方進行團隊合作。現在我們實現了這種轉變,這很不容易。
CBR:能否舉一個例子,來展示新供應鏈的好處?
梁耀榮:它最大的好處在于有效的營運資金管理(working capital management)。舉例來說,如果采購的液晶屏并非是銷售系統訂單要求的,會帶來兩個問題:第一是營運現金流的問題,所購的并非所要的,這既占用了現金,還導致企業需要動用更多的現金另外去采購真正所需要的,如果最后那些產品沒賣出去,現金流就“阻塞”了;第二,電子消費品的毛利潤率正在下滑,實際上,市場競爭十分激烈,平板電視的價格至少以每年24%左右的速度下滑。如果存貨一個月沒賣出去,相當于2%的損失。所以,低庫存、低營運現金流可以帶來更高的毛利潤率。
CBR:這種方法是否只適用于產量很小的時候?如果產量很大,也能使用這種訂單生產、低庫存的方法嗎?
梁耀榮:是的,也能適用于產量很大的情況。比如我工作過的飛利浦,它們非常精于此道,嚴格控制營運現金流被占用過多。最近你可以看到媒體報道一個日本公司正在大幅降價,就是要把庫存全都賣掉,減少現金的占用。從國內的情況來看,我們現在在這方面已經有了很多經驗,可以說達到了一個較高水平。
和以前相比,我們供應鏈的流程長度至少縮短了一半。
CBR:供應鏈管理和成本的透明性之間有何關系?
梁耀榮:供應鏈是由各種原料和貨物連接而成,而這些原料又都處于不同的時間點上,不同的時間有不同的價值。所以,供應鏈傳遞的是貨物在不同時間的成本,而非傳遞在預算中那個固定的價格。
一些公司的做法是,完全按照既定的預算來傳遞價格而不管市場變化,如果能盈利就盈利,如果虧本就只能虧本。這不是一種市場化的方法。尤其是在一個劇烈動蕩的市場,更不能這么做。所以我們通過供應鏈管理,盡可能縮短流程,這樣成本縮減而且更為可控。而一旦縮短了供應鏈時間,我們可以最快地發貨,賣個更高的價格(因為平板電視的價格一直在下行),這樣我們又提高了毛利潤。過去6個月當中,我們的毛利潤一直在穩步攀升。
CBR:如果將TCL的供應鏈管理和索尼、三星這樣的平板電視領先企業相比,您認為差距在哪里?
梁耀榮:我們6個月之前逐步改善供應鏈管理,對供應鏈管理的提升過程也遠遠還沒有結束,也正在尋找合適的公司進行標桿對比。不過從目前中國地區的情況來看,我們已經是在此方面還是做得不錯的。
其實有的時候,怎么做并不是秘密。在公司管理方法層面其實沒有秘密,唯一的秘密是,你能夠充分執行嗎?
為了做到多媒體的供應鏈管理,我們建立了很多流程,而要讓這些流程運轉起來,公司必須作出很多改變,為此,我們也做了大量艱苦的工作,大量的說服和討論,這些都是無法避免的。但現在大家都能理解并接受了這一觀念。所以說,員工都是講道理的,如果他們不能理解,他們就無法接受,但一旦理解了,他們很容易接受并執行。
CBR:你能說說關于和面板生產商建立戰略合作關系方面的事情嗎?
梁耀榮:三星是我們最大的戰略合作伙伴,最近我們還選了第二家廠商做合作伙伴。這兩家供貨商所供液晶屏占了我們全部需求的60%~80%。
今年“十一”長假的時候,我們在北京和一些液晶屏供應商進行了會談,他們和我們的業務單元負責人,以及地區銷售經理坐在了一起,談論明年的業務情況。他們給了我們穩定的屏源以及有競爭力的屏價格。此外,當客戶要求有變化時,他們也能根據我們的要求進行變化。而在一年前我們還做不到這樣。
CBR:今年TCL多媒體開始盈利,而以前虧了好幾年。你認為哪些因素促成了今年的盈利?
梁耀榮:如果說什么因素對扭虧貢獻最大,我想銷量和技術提升有貢獻,毛利潤管理當然也功不可沒,成本控制以及成本的標桿對比也有貢獻,這是最有貢獻的前三位。
以“目標導向”取代“部門導向”
CBR:你成為CEO之后,高管團隊新加入了幾個人?你的選人標準是什么?
梁耀榮:高管層面有3位,中級管理人員也有1~2位新來的。我認識他們,他們都是我的前同事,其中一個退休后過來幫我。雇傭他們的原因是:第一,我相信他們可以勝任這份工作;第二,我相信他們能夠很好地進行團隊合作;第三,他們會說中國話,盡管我自己的國語一般。
CBR:那么,您加入以后,管理團隊的薪酬激勵體制發生了什么樣的變化?
梁耀榮:高管的薪酬變化不明顯。較為明顯的變化發生在區域負責人以及各個部門執行層面的人員薪酬體系上。這些員工固定收入以前占比65%,變動收入35%,而現在則是固定收入占比70%,變動收入30%。
更高的固定收入,更低的變動收入。這好像是不符合邏輯。正常的邏輯是更低的固定收入和更高的變動收入。但在增長型的經濟和穩定型的經濟中,激勵模式也應該有不同。如果變動收入占比重過高,雇員們可能滿腦子都想著如何獲得獎勵,而忽視了基本任務的完成。我希望我們的雇員們不要太擔心自己的收入,而把大部分精力放在設定目標的實現上。
CBR:在績效考核制度上有些什么變化?
梁耀榮:作為公司領導者,我致力推動跨部門的合作,并將部門合作列為核心績效指標之一。我們鼓勵不同部門間相互合作,如果你遇到了問題,而另一個部門能夠解決這個問題,那么,請走出你的部門,和其他部門的人交流協作,共同找到解決方案。人們應該更多的“目標導向”而非“部門導向”。
CBR:推進部門間合作是否遇到阻力?
梁耀榮:實話實說,的確有困難,因為老的績效考核制度已經存在了很多年。公司習慣于在過去的獨立職能的基礎上運作,所以你很難讓不同部門的中層或底層人員真正合作起來。
我們的方法是,首先將部門合作因素納入部門領導者的績效考核指標中。這相對容易,因為我個人可以直接和他們溝通。比如一個項目出了問題,美國的銷售部門和中國的研發部門共同承擔這個項目,他們必須共同承擔責任而不是互相推卸。明年我們會有很多小項目來促進這種不同部門的管理層的合作。但是,接下來需要幾年時間把這個層面的合作延續到部門的中層。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國際化路徑再學習
CBR:請評述一下你們的四個市場。
梁耀榮:中國是最大的市場,正在持續增長;歐洲業務也在持續增長,我們依然相信這個市場可以帶來利潤;但北美現在看來不是很穩定,我們必須小心觀察和行事,新興市場則比較復雜,我們正在制定相應的策略。
CBR:戰略OEM有什么打算?
梁耀榮:我們還會繼續進行戰略OEM。因為我們需要提高產量來分攤固定成本、提高議價能力。今年我們的OEM業務開始從CRT轉向LCD,并從量上去的突破。我們還將繼續開發更多的客戶,為他們貼牌生產。按照計劃,在我們的總產量中,40%是OEM業務,60%是自己的品牌電視機。
CBR:您在飛利浦工作多年,現在又在TCL工作,根據您的觀察,TCL作為一個中國的國際化企業,它有什么樣的特質?
梁耀榮:“走出去”是中國企業的潮流。如果你看看那些世界級的品牌,沒有幾家是來自小國的。國際品牌多出自大國,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國內的業務是國際業務的基礎和后盾,到海外去發展需要很大成本,而國內的龐大業務有助于分攤這些成本。而且,國內的市場給了企業以“保護”,每個國家都在保護本國企業,即使在WTO規則下的“公平競爭”,本國企業肯定也被“更加公平”地對待。所以龐大的國內市場是中國企業國際化的優勢。
CBR:能否評價一下TCL目前國際化進展的情況?
梁耀榮:TCL的很多經理幾年前才開始學習國際化,當然與那些有著幾十年國際企業工作經驗的外國經理人有差距。但與國內其他企業相比,TCL還算不錯。事實上,到目前為止,究竟有幾家中國企業實現了國際化呢?很少,也就聯想、海爾那么幾家。連中國銀行(3.12,-0.03,-0.95%,吧)都沒有充分實現分行海外拓展,也就是說,中國甚至連金融機構這樣追逐資本的企業都沒有實現真正的國際化。所以我們不要認為自己已經實現了國際化,并沒有,我們只是在實現國際化的路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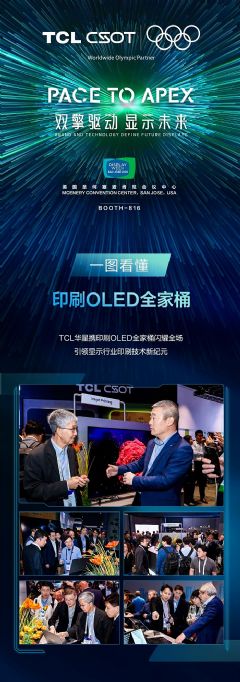











 康佳平板電視
康佳平板電視 創維平板電視
創維平板電視
 LG平板電視
LG平板電視 海信平板電視
海信平板電視 WAP手機版
WAP手機版 建議反饋
建議反饋 官方微博
官方微博 微信掃一掃
微信掃一掃 PjTime
PjTime